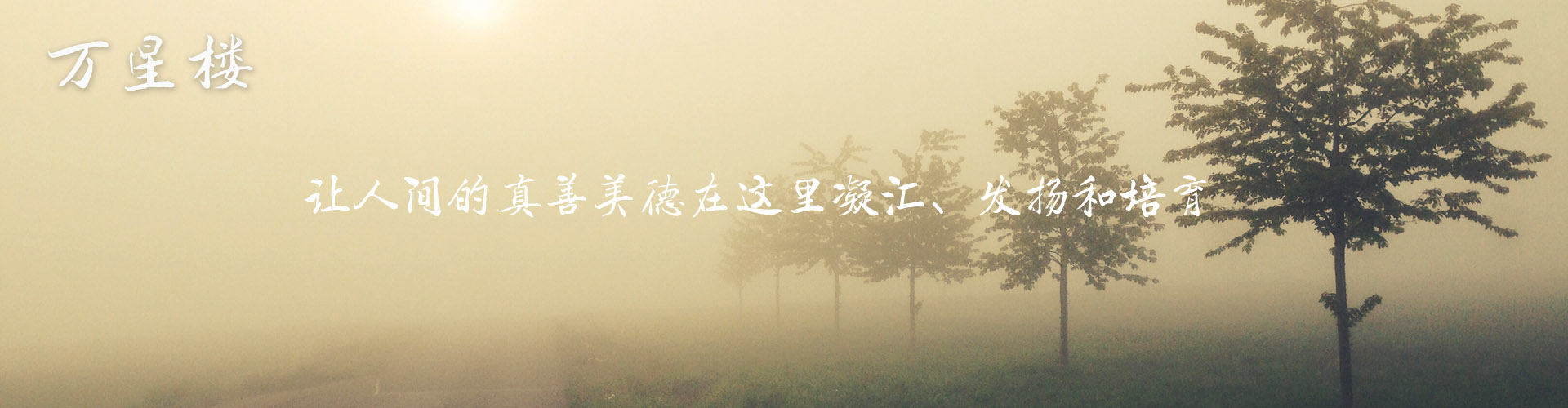群体的奉献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2051
群体的奉献
——十探罗辀重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事业,不只是职业。凡事业,必须要有群体意识,讲究整体效益。毛泽东指出:“一个百人的学校,如果没有一个从教员中、职员中、学生中按照实际形成的(不是勉强凑集的)最积极最正派最机敏的几个人乃至十几个人的领导骨干,这个学校就一定办不好。”①罗辀重主持的陶龛学校,每年在校师生好几百人,办学长盛不衰,效果日益显著,不仅因为有这样一批领导骨干,而且因为学校的创办人、教员、工友、学生、家长以及所有关心这所学校的人,大都是一些自愿的奉献者。这正是罗辀重自己带头做到,并要求师生员工都做到的:人人都要“勇于尽自己的职责”②;都要有“服务的精神”③。这“职责”,就是“奉
献”;这“精神”,就是“奉献精神”。
罗氏家族的奉献
陶龛学校是一所私立学校,1950年移交给人民政府时,校舍占地40亩,校产田租340硕,房屋百余间,藏书2万册,还有大量仪器、标本及其他教学用具。这些固定资产大都是罗氏家庭无偿提供的。1901年,陶龛先生之子、罗辀重之父罗申田置田租240硕,创办陶龛义学,1906年改名陶龛两等小学堂,1912年定名陶龛学校,先后以罗申田住宅画竹园、陶龛先生之侄罗穆青所住中义堂和罗辀重之堂兄罗季则住宅抚余山庄为校舍。1920年,罗辀重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来重主校政后,又加捐田租100硕为建校预备金,罗季则也将抚余山庄捐半兑半作为陶龛学校的永久校舍。1931年,陶龛先生之长孙罗仲渊见陶龛学校建筑经费困难,带头捐助大洋一百,又见学校图书馆图书不多,便将家藏旧书不下万卷搬到图书馆供师生阅览。当时的《湘乡民报》报道说:“象仲渊先生这样热心教育事业,既给我们以‘住’的教学室,又给我们以‘食’的书籍,岂不是我们的恩使,愿我同学们志志勿忘。”④
在半个世纪中,罗家先后有罗芳青(1907)、罗仲渊(1908)、罗穆青(1910代理)、罗辀重(1912)、罗季则(1914)、罗伯虞 (1917代理)、罗辀重(1920)、罗彦谋(1930)等七人出任陶龛学校校长(堂长)。他们主持陶龛校政,只讲“与”而不讲“取”。对于优良教师,他们高薪聘请,而他们自己除在学校吃饭外,分文不取。罗仲渊任陶龛两等小学堂堂长三年,组织教师认真做好教学工作,获得群众好评。他后来一直担任陶龛学校董事会董事,呕心沥血,积极支持罗辀重办好陶龛学校,1934年病故时还遗嘱拨谷百担交陶龛学校建立“仲渊图书馆”。罗季则为支持罗辀重为父申冤和出国深造而一度接长陶龛学校。为求教学环境条件之改善,他将陶龛校舍迁到自己的住宅,后来又将此住宅全屋归校。罗辀重曾代表陶龛学校向他赠送“廉义可风”匾额。罗彦谋热心教育事业,早在1918年5月便与罗君强自捐水田6亩,借用紫荆园,创办半日制的“求实通俗学校”,以“努力做人”为校训,招收农家失学青年57人,学费、书费一概免收,陶龛学校教师义务兼课,教材采用当时流行的《简易识字课本》、《简易算术》、《国民必读》等,深受群众欢迎。1920年,他又在罗辀重的倡导下创建“女子职业学校”,以“扫盲学技,移风易俗”为宗旨,开设缝纫、刺绣、编织、打袜等职业班,全日制教学。他在该校提倡一夫一妻制,提倡剪发放脚、破除迷信、废除跪拜礼节,严禁赌钱和唱淫戏,开设国语、算术、天文地理,并在湘中地方率先采用幼灯教学。1928年,陶龛学校组织校务委员会,他被推为主任委员。1930年被正式聘为陶龛学校校长,一直工作到湖南和平解放。他以校为家,几十年如一日协助罗辀重以“血性”育人,使陶龛学校誉满海内外。
罗家子女大多在陶龛学校读书后就以服务生的身份留校工作。查阅陶龛学校保存下来的4个学期的教职员名单,其中罗家子女就有罗光璎、罗光碌、罗绍业、罗绳祖、罗昭华、罗新华等20人。罗仲渊先生的四川籍女婿周炼伯亦在陶龛服务多年。他们自己做“血性的人”,又以“血性”育人。他们与校长、校董们一样只是义务工作,学校只管饭,不发薪资。他们的工作任务只比别的教师多,不比别的教师少。罗辀重的长女罗光璎在陶龛既当中学实验班的班主任,又当任课教师,一心扑在实验教学上。校友徐检常回忆说:“她为了主持办好这个实验班花费了不少心血。一是工作极端负责。每次学生搞劳作实习,她都亲临现场一起参加劳动。有次去壶天煤矿参观学习,尽管天气炎热,步行又走了大半天路,她不顾自身疲劳,不怕苦不怕脏,仍和同学们一道下隧道,钻井巷。她讲课一丝不苟,所讲授的历史课程,以故事形式讲,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又极易记忆。二是关心同学胜过关心自己。她讲话精炼,言短意深,善于做思想教育工作,同学们都很服她。班上出现了矛盾,只要她出面就迎刃而解,所以班上同学之间相互体贴相互谅解,团结气氛很浓。班上的同学全是寄宿,从住的、吃的,乃至用的,她都照顾得体贴入微,同学们都称她既是师长又是慈母。三是对自己要求严,军人作风说干就干,干净利落,很讲究务实,为人直率,态度谦和,从没有一点架子。”
教职员工的奉献
在罗重纪念馆里收存着校友捐献的1949年1月的陶龛学校聘书一份。聘书印着受聘者必须共同遵守的信条有9:1、施教不限于校内,教学不限于课中。2、随时随地随人负训导之责,俾教育效率得以增加。3、对儿童一视同仁,并遵法令,不用体罚。4、能和学生同甘苦,共患难。5、率先实行团体生活规律,打破个人私生活。6、以身作则,实行新生活规约。7、对同工推诚合作,一切以大局为重,不轻易发生口角争执,减少人事磨擦。8、对有关教育事件,当仁不让,不互相推诿。9、出席有关各种集会、俾明了整个计划,以利进行。这9条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精神也体现在1943年罗辀重所拟《聘师之条件》中。陶龛学校的教职员工都熟悉这9条,并严格遵守这9条。
凡在陶龛学校服务的教职员工人人都对事负责,所以事无不举,绝无相互推诿敷衍塞责之弊。“他们对于事务的分掌是这样的:几个有历史关系而在校服务较久的,当然比新聘来的或远处的熟悉情况一点,所负责任就多;同时,他所负的教授责任,却同各教师一样,是平均支配的。至于教师呢,除所担教务之外,仍轮流值日:如晨操指导、清洁指导、周报指导、商店指导,点名、请假,夜中督课等直接与学生有关之事,固不待言;有时关于出纳款项,书写公文表册等事,都本合作而不分工的精神,不分畛域的做。”⑤也许有人担心:“这样一来,岂不会事务纷歧,无人负专责?”在陶龛,这种担心是多余的。因为在人人都讲奉献的群体中,是不会出现无人负责的事情的。陶龛的教员有许多戏称,诸如“兼职式”的、“校役式”的、“保姆式”的,他们劳苦奔忙,有时连吃饭屙屎的时间都腾不出,“然而偏偏好整以暇,每日下课后,学生打球队中,着棋丛里,总有所谓‘师’的点缀期间,至于撑渡船,骑脚踏车,弄乐器,踢毽子,更是日常必修课,都包括在‘百忙’中的。”⑥他们“忙中有苦”、“忙”中更有 “乐”。因为“忙”的是奉献,而不是“索取”,其乐无穷。
陶龛学校“教员均属学识优良,勤谨供职”⑦。他们大都是师范毕业生,经过专门训练,有不少人还是大学生或出国留学生,个个学识渊博,人人教学认真,工作细致。“女教员黄朴英教授高年级国语,教态沉静,演解详明”⑧;“女教员屈成惠积劳成疾,病故于校;教导主任杨久萱,对每年五六百在校学生,均能一一叫出名字;石璇吉先生管伙食,刘采叔先生管福利社,其和蔼可亲的态度,令人难忘”;“教员肖光安、罗昆吾精心研究,周炼伯、罗绍业、罗绳祖等既肯负责,教望亦嘉”;“总之,该校教员,均能同心一德,力图尽师保之责”⑨。
古人云:经师易得,人师难求。陶龛学校教职员工以“血性”育人,首先自己“血性”做人。该校教员品德高尚,思想进步。陈素、李品珍、刘汉初等一大批中共地下党员先后在该校任教过。刘楚威、刘佩旬、罗昭华、罗新华、刘汉英、罗光碌、黄朴、胡刚父、朱道兴、罗宗藩、成之恒、万民裕、刘常仁、罗耀星、罗光旗、李泽湘等一大批先生的学识风范,至今在许多陶龛校友的脑海中记忆犹新。他们爱生如子,为贫困学生垫付学费,雪雨天为远道来校的学生打温水洗脚,习以为常。“以身作则”是他们最重要的共同守则。凡要求学生做到的,教职员工首先得自己做到。陶龛学校不准学生抽烟、嗜酒,因此,陶龛教职员工都戒烟戒酒。校友邓志强回忆说,有个姓刘的先生,年纪很大了,抽水烟上了瘾,怎么也戒不掉。为了给学生做出榜样,他强制自己尽量少抽,即使抽一回,也是躲起来抽,抽过之后立即把水烟壶藏在柜子里。但他并不向学生隐瞒此事,而是不好意思地主动请求学生们的谅解。1946年,湘中乃至全国,自然灾害连绵。陶龛学校由于率先实行二五减租,经费奇缺,连给教师发薪的谷也不够。但教师们毫无怨言,他们中许多人表示不领薪谷,尽义务工作。他们还带头向灾区捐款。该年5月31日的《湖南日报》转发中央社讯称:“湘乡私立陶龛学校全体师生为响应节食救灾运动,捐款12万元。”
学生的奉献
有人云:“学生视学校如逆旅、如寰柜,而主校政者亦率以逆旅主人、寰柜自居,交易而退,彼此不相关也,久矣。”然而,陶龛学校则有异于此。该校“形成了全体师生的家庭”⑩,“学校对待学生均带家庭意味”⑾,“师生大有父兄子弟之情”⑿,主校政者以校为家,教职工以校为家,学生也以校为家。他们时时处处都不忘这个家,都在尽自己所能奉献着。陶龛学生的奉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出力。在陶龛学校,凡孩子们能做的事,都放手让孩子们自己去做,这不仅锻炼了他们的才干,而且培养了他们奉献的精神。陶龛的运动场是师生开辟的;陶龛博物馆的动植物标本,有许多是学生假期采集的;陶龛中学实验班的房子是学生自己盖的;陶龛的各种职业陶冶活动小组乃至消费合作社的帐目,也是学生们自己管理,他们在经营实践中既体味了当家的艰难,学到了理财的本领,也培养了廉洁奉公的品性,还创造了联络人们一起过和谐生活的人际关系。
二是捐钱。陶龛学校于1929年为建图书馆和购置《万有文库》第一次向社会募捐,此后1931年为建筑“爱迪生院”、1936年筹建建校“三十周年纪念堂”、1946年为建筑“造血楼”等多次发起过募捐。这些活动均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特别是学生家长的慷慨解囊。有些项目的捐款还略有剩余。《陶龛年鉴》上记载有这样一件事:1943年9月7日,陶龛肄业学生李维吾在家病死,死时,念念不忘学校,其父李暑安专程赶到学校,捐教育基金500元,为子留念。陶龛学生还经常开展“节省零花钱”奉献“公益”活动。1933年,该校学生自治会决议,“节省于身体无益有损的零星钱来作救国飞机捐款”。1940年6月天旱,陶龛学生在组成义务车水队开展救青苗运动的同时,还节省一旬之中餐费,津补本校所在地之“友助团”办理平粜达一月之久。1943年“四四儿童节”,陶龛学校开始“日行一善”活动,发起急赈湘北难童运动,一日之间捐得国币5500元。这些钱大都是学生们的“零星钱”。
三是毕业留念,陶龛学生毕业,人人都有过“临去低徊,既去顾恋”的切身体会。毕业各班往往或置图书或购物什或施建筑留纪念。据《陶龛年鉴)记载,自1933年暑假,该校22班毕业生在校内建“念念亭”为留校纪念后,几乎年年都有毕业班留下纪念物。现列表如下:
|
年份 |
毕业班次 |
留 校 纪 念 物 |
|
1933年 |
22班 |
念念亭 |
|
1934年 |
23、24班 |
钟形喷水池 小篮球场 |
|
1935年 |
25、26班 |
乌的家 总理临终遗言碑 |
|
1936年 |
27、28班 |
日晷台 八用钟 |
|
1937年 |
29、30班 |
旗杆 三十周年纪念堂横梁 |
|
1938年 |
31、32、33班 |
三益路 三益路上雨盖 |
|
1939年 |
34、35、36班 |
纪念亭外亭子 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眺望楼 |
|
1940年 |
37、38、39班 |
砌纪念堂四周石阶 装办公室天花板 建“螺旋亭” |
|
1941年 |
40、41、42班 |
钉“纪念亭天花板” 做中院灯塔 · |
|
1942年 |
43、44、45班 |
砌“游戏场石堰” 置办公桌、椅 |
|
1943年 |
46、47班 |
做图书承尘板 |
|
1944年 |
48、49班 |
做中院天井V字栏杆 |
|
1945年 |
50、51班 |
防空洞工程 校友会公文柜 |
|
1946年 |
52、53班 |
纪念堂讲坛桌 校友楼一面玻璃 |
四是校友服务。陶龛学校于1927年正式设立校友服务制,从品学兼优而又无力升学的毕业生中挑选一部分留校服务或选送去读书待毕业后再回校服务。这既解决了学校师资问题,又解决了一些贫困学生的就业问题,同时更加密切了学校与毕业生的关系,一举数得。现在台北的杨烈芬校友曾两度服务母校达6年之久。爱母校,爱家乡,在陶龛校友中形成了风气。凡在陶龛求过学的学生,不管走到哪里,总记着把动植物和矿物标本带回母校,把书刊寄送给母校图书馆;学校经费困难,总有校友发起募捐。1937年设立了校友返校节(元旦),创建了校友楼,更加密切了校友与学校的联系。1941年,校友罗绍业等倡仪编印罗辀重先生教育言论集,后由校友总会发起捐款,于1944年以《老青集》的书名出版。陶龛的“爱迪生院”和“三十周年纪念堂”,主要是旅居国外的校友捐资兴建。1946年,校友宋希濂 (国民党高级将领)以其父宋樾山的名义捐款为陶龛营建“造血楼”(即四十周年纪念堂),竣工后命名为“樾山学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修水库,陶龛学校被拆迁。八十年代,国内外陶龛校友强烈要求恢复重建陶龛学校,设立罗辀重纪念馆,得到了人民政府的重视。校友杜佩玖(武汉工学院教授)主动为学校的重建设计了图纸。1984年到1986年,在重建陶龛学校和创办罗辀重纪念馆期间,有500多位校友捐赠了百多件文物、礼品、纪念品,捐款2万多无。1987年后,海内外校友不断赠礼捐款筹办校庆,设立罗辀重奖学金。这些校友有在台湾的、香港的和在大陆各省 (市)的,也有在美国的,巴西的和印度等地的。
奉献群体的核心
1933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视察员吴研因在《视察湖南教育报告》中,说他视察了长沙、衡阳、益阳、常德、桃源、湘乡等地10所公私立小学。他把这些小学分为甲、乙、两三等,唯湘乡私立陶龛小学“居甲等”,“可称为首屈一指者也”。他还指出:陶龛“校董兼教员罗春驭,实为是校之台柱”。吴研因对陶龛对罗辀重的评价是客观的,公允的。陶龛学校举世瞩目成就的取得是因为有陶龛师生员工这样一个奉献群体,而陶龛师生员工之所以能够形成为一个奉献的群体,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因为“台柱”罗辀重这个核心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吸引力。罗辀重的核心凝聚作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是专心一志的献身精神。1920年,罗辀重从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回国,不要官,不要钱,婉辞各种邀请,直奔家乡主办陶龛学校,一干就是几十年。曾经和罗辀重讨论过师范教育改革的王奠球先生说:“罗辀重是全心全意办陶龛,一生一世不做官。”1991年,《湖南教育志》主编刘欣森先生在《陶龛九十校庆文献序》中说:“近几年,我在编纂《湖南省教育志》的过程中,发现清末、民国年间湖南的基础教育相当发达,许多时候在全国各省居于前列。而湖南基础教育之所以发达,主要靠一大批学界栋梁的奔走呼号、毁家兴学、惨谵经营和循循善诱。这些学界栋梁如熊希龄、杨昌济、胡元炎、陈洞森、朱剑凡、徐特立、曾宝荪、曹典球、何炳麟、孔昭缓等先生,屈指成十盈百。唯独罗辀重那样毕生致力于农村小学教育的留美学生则数不出第二位来。”罗辀重于1912年正式开始投身乡村教育,直到1950年殉职教育,中间一度到哥伦比亚大学深造,也是为的攻读教育办好乡村学校。他的全部家产变成了陶龛的校产。一个留美学生,义务献身乡村教育40年之久,其“足迹一学期还难出校门几次”⒀,这种专心一志的精神恐怕无人不会不“因此十分感动”⒁。
二是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罗辀重的家人就住在陶龛学校后面,但他一心扑在学校工作上,很少回家。校友罗徵肇回忆说:“罗辀重先生除每旬末日间或回家与家人团聚外,其余时间均留宿校内,与全体师生共同生活在一起,全副精神专注在校内的大事务与学生的生活起居上,并能以最敏捷而果断的方式,解决任何困难问题。”对陶龛学校事务,不论巨细,罗辀重都要亲自规划处理。他主持全校事务,仍兼教英语、摄影、语文等课程。《陶龛旬报》,从组稿、编排、校对,都是他一手经办。每期旬报,他都要自己至少写一篇文章;句斟字酌。旬报一度采用石印,张张都是他用毛笔书写。每周劳动课,他都带头劳动,和师生一起担砖、递瓦。寒暑假,他经常步行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做家访。在陶龛,他每天起得最早睡得最晚,有时还亲自吹起床号和熄灯号。他每晚都要下寝室查铺,从这个寝室到那个寝室,一个铺一个铺的查。发现有学生踢开了被子,他给盖好;踢开了蚊帐,他绐放好。对个别尿床的学生,他则记在心里,及时叫他们起来小便。他“劳苦终日,毫无倦色”⒂,其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堪为师界楷模。
三是锐意革新的胆识作为。罗辀重认为教育的最基本任务是为后生“造型”、“造血”。他主张学校教育必须改革,不能造出那种“没有主张,怕用思考”,没有“创造精神”⒃型的和没有“血性”的人才,而是要培养具有“血性”气慨的“善用精神于创造上”⒄的新型人才。因此,他反对那种“对于一切事体,喜欢因袭,安于故常,情愿做一个思想的随从者,不愿做一个独立的研究者”⒅;“他最讨厌陈旧,学校里的陈设,这个学期是这么陈列着,到了下一个学期却必得要换一换新花样”;“他做每件事情都是迎头赶上新的趋势去”⒆;他对“群体德智美”五育一一进行“价值重估”,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他对“近代教学做的各种新法,无不具体采用”⒇。校友肖杨回忆说:“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电影是在陶龛学校,第一次见到收音机是在陶龛学校,第一次看见和弹奏钢琴也是在陶龛学校”;在陶龛学校,“血性”校训和“旬日制”,独具一格,“施教不限校内,教学不限课中”的教师聘约,亦特别新颖。罗辀重的这种锐意革新的胆识作为无不令人佩服。
四是真诚待人的“血性”品格。罗辀重“以身作则”,按照“血性”校训“待人”、“律己”,在陶龛被称为“血性”的标杆。他要求教师做到“脱下长衫,放下身份,手脑并用”,“不要再存轻视农工之心理”(21),自己则首先做到。陶龛学校以校租为基本收入。校庄的田地也是租给佃农种的。当时,佃农是最让人瞧不起的,在陶龛却受到罗辀重的特别尊重。每年佃家送租,他总要亲自到河边去接,遇到旱涝灾害,他总是要带领师生到田地帮助抗灾,宁可举债办学,也要主动减免田租。他对教职员工亲如兄弟,对学生亲如子女。遇有校友返校,总是热情接待,使每个校友都有“女回娘家”的亲切感。他认为,“吾国是穷国,我们要以经济的方法,办最有效率的事情”(22),因此,十分注意节省办学开支。他在陶龛学校坚持不设门卫,一来是耽心“门卫以貌取人”,“不要见的伪君子”可能“引进来”、“而那些贫苦的老百姓好不容易到这里”,又可能被“拒之门外”,二来也是为了节省开支。那时,到陶龛的部、省、县督学及各式各样的知名人士不少,他一概不设席招待,只有种校庄田地的佃户来送租谷时才办酒菜以示慰劳。社会各界的捐助是陶龛办学的重要依靠。这些捐助的奉献者,都希望自己的奉献能真正发挥作用。罗辀重最能遂其心愿。他对待任何奉献,首先做的就是及时按奉献者的心愿使用起来。捐助的图书报刊一到手,他便立即陈放到图书馆、阅览室,开架出借。他自己更是发奋地阅读,并把教学有关的内容勾画出来,分送给教师们研讨。每次校友发起募捐新建校舍,他不仅坚持专款专用,而且总是一边筹款,一边施工,力求当年就建成用上。抗日时期社会各界的捐款大多是为难童、为抗日将±的子女提供就学基金。罗辀重在陶龛每期尽力招收这类学生,捐款如有剩余,便存入银行或投资于实验农场和消费合作社,使死钱变活钱,既保持捐款价值,又利于学生“职业陶冶”活动的开展。其次,他对待任何奉献,不论捐助数额多少,也不论价值高低,一律登报鸣谢。第三,由陶龛学校发起为“文化劳军”、“救灾”等社会性捐助活动,其组织募捐的各项费用均由陶龛学校垫付,决不在捐款中开支。1943年,该校“响应文化劳军而募得巨额捐款,涓滴归公,其爱国热情实属难能可贵”(23)。联想起今天我们有些负责承办“救灾”、“希望工程”等捐款的部门和单位,他们的吃、喝、用、补助均要在捐款中开支,怎能不叫奉献者心寒。罗辀重之所以能成为奉献群体的核心,他真诚待人处事,专款专用,“以付捐助者之盛意……总期于捐款不致虚掷”(24)而温暖奉献者的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989年,一位台湾校友为纪念罗辀重百龄诞辰发表《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一文。他写道:罗辀重“以牺牲奉献的心志办学校”,“舍弃高官厚禄而不为”,“全心全力投入陶龛”,“从学校章程的厘订,校舍的逐年扩大,各项设备的不断充实,以及教学计划的适时创新研定等等,无不巨细躬亲;但他不要任何名义,校长一职则由同族晚辈罗彦谋先生担任”,“如此牺牲奉献,后来地方人士及师生就送给他一个‘无花果’的绰号。意思是说他不要享受学校‘开花’时鲜艳烂漫的光耀,只顾如何奉献硕壮丰盛的美好果实”。我想,如果我们能有千千万万罗辀重这样的“无花果”,千千万万陶龛学校这样的奉献群体,我们的教育事业以至我们的一切事业,何愁不兴旺发达。
1997年5月
① 毛泽东《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② 1943年7月8日《陶龛旬报》
③ ⒃⒅(22)1936年《长沙市教育》创刊号“师范教育放言”。
④ 1931年7月29日《湘乡民报》。
⑤ ⑥1937年《湖南教育》“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
⑦⑧1935年1月12日《湘乡民报》。
⑨⑿1932年1月29日《湘乡民报》。
⑩ 1943年5月8日《陶龛旬报》“李庆元先生来信评陶龛”。
⑾1941年2月1日《湘乡民报》。
⒀1936午《长沙教育》创刊号·编辑的话。
⒁1937年17--18期《楚风》。
⒂ 1929年4月28日《湘乡民报》“读了‘血性’之后”。
⒄ 1939年5月18日《陶龛旬报》。
⒆1936年《沩风月刊》“我所知道的罗辀重”。
⒇1931年2月7日《湘乡民报》“陶龛别具精神”。
(21)1943年4月18日《陶龛旬报》“读书人的态度”。
(23)1943年1月24日《湘乡民报》。
(24)1940年8月8日《陶龛旬报》。
发布时间:2008/10/9 【打印此页】
上一篇:“血性”罗辀重和陶龛学校
下一篇:乡村教育改革的成功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