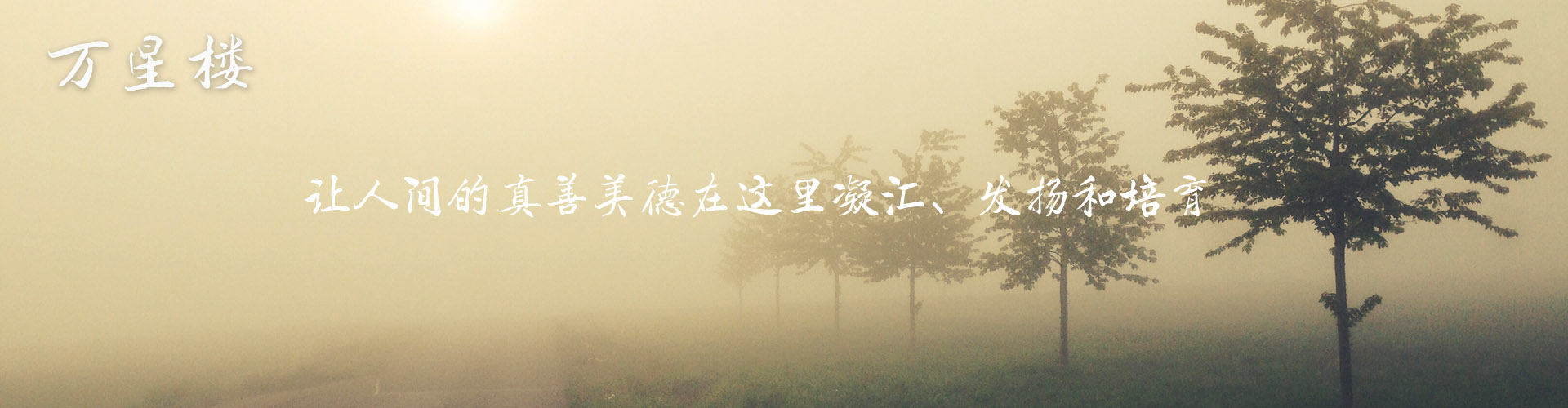关于朋友的话题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1529
关于朋友的话题

我这人生来就爱交朋结友,从幼儿园至今,近半个世纪了,阅人无数,只要能进入我的“法眼”者,都设法引为同道,哪怕有时有点委曲求全,也不计较。粗粗算来,我结交过的的友人总有好几百吧,老的,70,小的,与我女儿差不多,20多一点,最早的,将近40年,最近的,几天。单位最近调进一位老师,学中文的,写作水平好生了得,早几天他送我一本他的作品集,我一读,立即被镇住了,于是很谦虚地将我写的东东向他求教,他却说不错不错,佩服佩服。我又添一知己,当然激动万分,想,以后的日子里能经常与他“互相吹捧、共同前进”,也不坏。当然,随着岁月的流逝,能长期保持联系的,不到那“无数”中的十分之一了。不过,数量减少了,“质量”却得到了空前的提高。从某种意义上看,友情之可贵,不会逊于亲情。我只要有了空闲时间,立即呼朋引类,一瓶老酒、一杯清茶、一包香烟,边喝边抽边聊。在缭绕的烟雾中,口无遮拦,不怕宇宙之大、不嫌苍蝇之微,上到联合国,下至本单位,无不成为扯谈的本钱。我们或交流信息、或评论时事、或藏否人物,讲到激动处,信马由缰,甚至胡说八道,也在所不惜,只要不负法律责任就行。聊着聊着,不觉到了深夜,想到次日还要上班,就带着微醉,散了。有天冬夜,白雪飘飘,忽然想起一个多日不见的忘年之交,就掏出手机,问,近来活得如何?朋友比我更兴奋,说,三言两语讲不清楚,我马上过来。于是花了三十元打的赶到茶楼,天南地北地海聊,三个小时一晃而过,凌晨两时,才恋恋不舍地分手。我回家后躺在床上,还兴奋不已:哈,“此趣谁云不快哉”?出差在外,几天不见朋友,心里慌得很,有一次到海南,下飞机后不久就接二连三地“批发”短信息:“天高云淡,椰风送爽,三亚仙境,梦幻人间。”收获到的也是种种美好的祝福,那种心境啊,实在是妙不可言。
我为人随和,善解人意,更因为喜欢关注、传播和分析“美国校园枪击案”、“邯郸农行金库被盗案”一类新闻,大多数场合下,朋友们自然以我为核心,屏住呼吸,听我眉飞色舞地滔滔不绝,哪怕我有时讲的数据等并不十分严谨。我也在一定的范围内喜欢帮助朋友,有人遇上了经济上的难关,我可以毫不犹豫地送上三百五百。我也经常与朋友吃饭后主动买单,坐的士抢司机边上的位子,等等。我还有一个很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当朋友升了官、发了财,我就像自己升了官发了财一样高兴。当然,我绝不从此就会仰视着政治上发达了的朋友,很小人地请他帮我在组织人事部门美言美言,以便我在仕途上更迅速地茁壮成长,或者幻 想某天接到某友打来电话,要我到他当董事长的财务室去领取几万元的支票并反复声称不要还。
谈了这样多的“优点”,也得解剖解剖自己与朋友交往时究竟还有哪些毛病和缺点。我在一座不大的城市长大,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一些小市民的不良气息,还有,不到十六岁便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可惜效果十分有限,不可救药地具有了中国农民那种目光短浅、谨小慎微的“局限性”,比如花钱放不开手脚,在私家车越来越多的今天还不敢财大气粗地买车,有事外出,宁愿厚着脸皮要求朋友接送;享用饭局后经常不顾朋友们责备的眼光将剩下的菜打包,等等。我有时有点小心眼,哪怕是在博客上有并不认识的文友指出我文章的不足之处,如果我认为他讲得没道理,要不舒服好一阵子,等等;我为人不算小气,但也不很“大气”,比如,如果哪位朋友患了肾衰竭之类的重症,需要几十万才能挽救生命,我可以帮他到社会上去呼吁、去募捐,自己也能勇敢地捐出个千把块钱,但是要我散尽千金去救他,至少在目前还做不到。再比如,如果某天与朋友一道在街上散步,一群歹徒拿出明晃晃的尖刀逼向他,我会边跑边用力呼喊:赶快抓坏人,赶快抓坏人,并随即拨打110,但要我挺身而出扑向歹徒,会犹豫不决,哪怕是冒着别人说我“见死不救”的风险。怪只怪我贪生,不能为朋友“两肋插刀”。 (当然,如果只有个把歹徒的话,我还是会考虑找个棍子之类的家伙进行英勇搏斗的)
我是独子,母亲将我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重要。我从小就娇生惯养,除了一张寡嘴,肩不能挑手不能提,被迫下乡后,一天到晚都打不起精神。队里出工挑牛粪,别人挑三担,我最多两担。但我又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读小学起就喜欢出风头,设法引起公众的注意,有几次在公开课上主动举手发言,老师表扬了一下,我就头脑发昏,不认识自己是谁了,后来逐渐发展为不举手也要强行发言,甚至很不礼貌地当场指出老师的知识性错误,屡屡破坏课堂纪律,为此多次被老师警告并强制写检讨。本性如此,要改也难,与朋友交往,我总是充当“劳心者”的角色。“君子动口不动手”,动手的事,经常是由朋友代劳。72年冬天,生产队要求我们知青上山背树,山路弯弯,一棵大树有百多斤重,我与另一位知青朋友抬一棵,还没到山下,我早已汗流浃背,气喘不止,就是把牙关咬烂,无论如何也挪动不了半步。那位朋友看我可怜,说,我一个人来试试看,说完,独自背着它,踉踉跄跄地朝山下走去,后来,他的身子疼了半个月。我无比内疚,赶紧到大队供销社买了一包“劳动牌”孝敬他,以后,干较重的体力活时愿意做我搭档的自然越来越少。三十多年了,知青聚会时聊起这桩往事,还大笑不止。
与朋友在一起时,我自作多情地认为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负有更多的责任,自觉不自觉地充当了他们的导师,没料到天外还有更辽阔的天空。某年某月某日,一张姓朋友对我说,某中学一位姓马的高中教师是个真正的读书人,学问可以抵得上几个博士。我将信将疑,于是在张朋友的带领下会马老师。一进马家我就傻了眼,只见书房里各种书籍堆到了天花板,随便翻翻,都作了批注,可见主人不是在附庸风雅。落座后不久,就进入了“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等时髦的话题。马老师仔细地倾听了我的分析后,看来并不满意,但顾及了我的面子,没作过多的评论。他从历史到政治、从文学到美学,一口气谈了三个多小时,真是髀阖纵横,字字珠矶。他虽不无偏激之处,但能达到他那种水平的,我估计当今中国的知识界并不多见,以后,我们成了无话不聊的好朋友,当然,在他面前,我始终不过是一个恭谦的小学生,哪怕是当着我的一大群粉丝,只要他开口,我会知趣地闭上鸟嘴。他调到深圳已经十多年,早几年回到我所在的这座城市,在我家小住三天,那是我十分幸福的时光。我从他那里吸收的知识的营养,够挥霍好一阵子了。
我始终弄不明白,有的人为什么除了亲人,没有任何知心的朋友。我虽然尊重他们对生活的选择,但我根本无法想象我自己没有朋友的日子该怎么过。写到这里,接到好友的电话,说今天是周末,是否到茶楼聊聊天,谈谈一周来各自的所见所闻以及或喜或悲的精神历程,我说好的。关于朋友的话题原打算还要拖上一个“光明的尾巴”,现在不得不就此打住了。
发布时间:2007/5/2 【打印此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