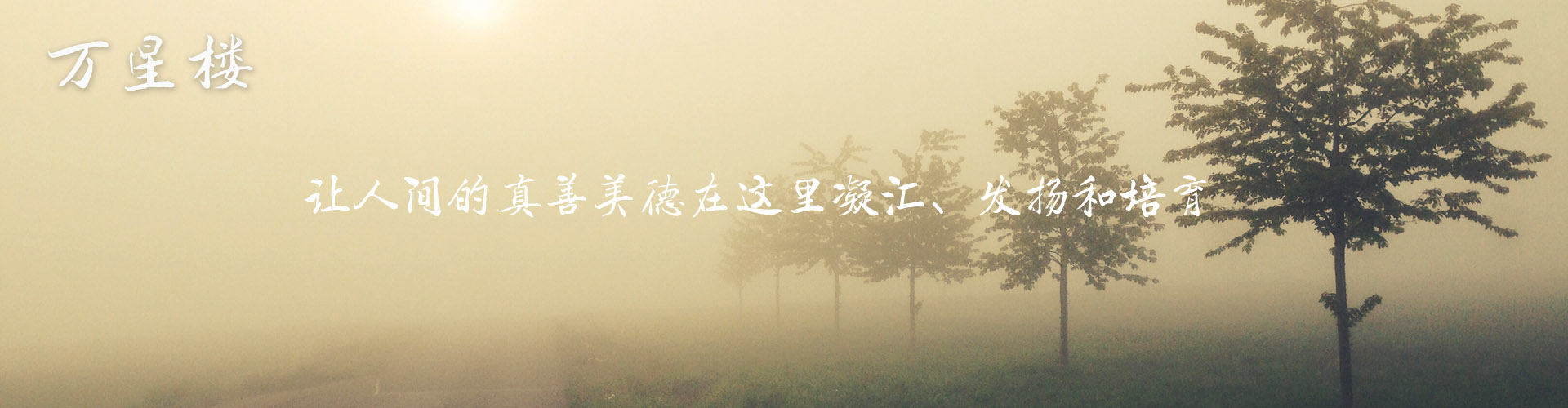第一章 “素养教育”的应运而生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教育的革命”, 提出了“普及教育”、“终身教育”和“全面发展”的三大目标。经历一个多世纪后,虽然“普及教育”在有些国家和地区已基本成为现实,但三大目标的全面实现,仍被人们视为“梦想”。而早在半个多世纪前就在一个局部地区实施“素养教育”,把世界“教育的革命”的三大目标全部变为现实的人,却至今很少人知道。
第一节 不只是“梦想”,也有现实

世界上的人类,所处地域不同,肤色不同,种族不同,语言不同,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均有所不同。但既同为人类,就必定有共通的地方,教育就是这样。
古代的世界教育,基本上有三种模式。一是以“科举制” 为特色的古代中国教育;二是以《吠陀经》为基础的古代印度教育;三是以军事体育为中心的古代希腊教育。而这三大模式的教育虽各具特色,却有着共同的标准:第一,只有部分人能够享受教育;第二,基本上都是独裁式的,死记硬背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世界近现代“教育的革命”也有着共同的目标。
世界近现代教育的革命,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发展应运而生的。
这场革命首先以“新学校运动” (也称“新教育运动” )的形式在欧洲兴起。1889年,英国雷迪首创阿伯茨霍尔姆新学校,提出将上层社会儿童培养成智力、能力、体力、手工技巧和敏捷性均得到发展的完美新人,主张学校应该是一个真实的、实际的,儿童能在其中发现自己的小世界,学校教学工作须与实际生活结合,学生智慧的发展须与体力的发展相结合。1898年,法国的德莫林,又仿照雷迪开办罗什学校,突破法国古典教育传统,在学校开办工场作业,使学校充满快乐自由的空气。与此同时或稍后,德国人利茨,瑞士菲利耶尔等都开办了同类型学校。新学校遍布欧洲各国,形成为广泛的新学校运动。
1912年,国际新学校事务局在瑞士成立,成为各国新学校互相联络的中心。1914年,新学校传入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新学校几乎遍布全世界,涌现了杜威等一大批现代教育家。在德国,企业家依米尔默特(Emil Molt)邀请鲁道夫·史代纳,根据人智学的研究成果,于1919年在斯图伽达(Stuttgart),为他的香烟厂工人的子弟办一所学校,并以工厂的名字 Waldorf Astoria命名为Freie Waldorf Schule(德语华德福)。在中国,就有陶行知创办晓庄师范、罗辀重主办陶龛学校等。
这场以新学校运动为形式的世界“教育的革命”, 已经进行了100余年,实践经验和理论原则不可谓不丰富。1915年,瑞士菲利耶尔就总结出30条,其中包括学校应有优美、舒适的自然环境与设施;要注重学生生活、学习的自治制度;要注重体育和培养学生智力,并发展儿童内心道德;要设置发展学生双手能力的手工劳动课程,等等。1919年创立的华德福学校教育,配合人的意识发展规律,阶段性针对意识来设置教学内容,让人的身体、生命体、灵魂体和精神体都得到迎合和发展。1921年,法国的加布雷市成立新教育联谊会,次年正式颁布章程,提出了新教育的七项原则:增进儿童的内在精神力量;尊重儿童的个性发展;让儿童的天赋自由施展;鼓励儿童自治;培养儿童为社会服务的合作精神;发展男女儿童教育间的协作;要求儿童尊重他人与民族,保持个人尊重。这个章程随着世界政治经济形式变化而不断修订。1932年,联谊会章程突出通过教育改良社会的要求,提出教育要使儿童领会当时社会经济的复杂性。1942年,联谊会又通过《儿童宪章》,突出所有各阶层儿童应平等享受义务教育,以符合世界性普及教育的要求。1966年,新教育联谊会改名为世界教育联谊会。
这些“教育的革命” 的理论原则,在世界各国的教育家那里有不同的说法和做法,但他们的目标主张是大体相同的:第一,主张所有的儿童都应受到教育,这是人的权利(普及教育);第二,主张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终身教育);第三,要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
然而,100余年来,世界教育界一直未发现有人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很好地实现这些主张,以致1998年上海三联书店在再版《学习的革命》一书时,说:《学习的革命》是每一个人迈向21世纪的“护照” ,而“教育的革命” 却还是我们的“梦想” 。
其实,世界教育革命三大目标的实现,早已不只是“梦想” ,也有现实。半个多世纪前的中国,早就有人在一个乡村学校实施“素养教育”,成功地实现过世界教育革命的三大目标。
这个乡村就是湖南腹地的白鹭湾(今属娄底市经济开发区大埠桥办事处),学校的名字叫陶龛,主持陶龛的人叫罗辀重。
20世纪20-40年代,由于有实施“素养教育”的陶龛学校的存在,白鹭湾一带的学龄儿童没有不入学的,年长失学的没有不复读的,“外省子弟,亦多响往就学”;学校“影响所及,乡邑风俗,为之转移”(《华学月刊》), 乡民们大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睁大了眼睛”;当地交通、经济、文化等许多方面的落后面貌得到改变;晏阳初所希望解决的“无教”和“娱教”问题,在白鹭湾一带得到了成功地解决,这里人人拥有美好的人生。如今,白鹭湾一带七八十岁以上的老者,和散布在海内外各地的陶龛校友,对少时所见白鹭湾之繁荣景象,无不津津乐道,无不生出怀念之情。
然而,1950年罗辀重离世后,陶龛学校不复存在;罗辀重及其“素养教育”的思想观点与实践经验也随之被埋没。直到1978年,改革的春风在中国大陆吹起,罗辀重才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里给抬出来。1989年,全国第七届人大安徽代表、陶龛校友王工,向全国人大递交了一个关于“发掘利用罗辀重教育思”的提案,提案被国务院转到了湖南省教委。据说湖南省教委很快就组织人写出材料给予了答复。1999年,肖华先生在 “罗辀重诞辰110周年纪念暨《罗辀重文集》首发式”上的发言,对罗辀重的被发现做了较为祥细的叙述。他说:
回顾这十几年来为恢复陶龛学校和研究罗辀重教育思想的艰苦奋斗过程,除了各级党政领导的正确决策和大力支持外,李如初、佘国纲先生以其个人的努力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身体力行,克服了种种困难,带动和影响着周围一大批人。正是他们不懈的努力,才取得了今天令人刮目的成果。
李如初先生在陶龛求学、服务前后不过三年,但受主持人罗辀重先生教益特多,受陶龛“血性”教育颇深;踏入社会后,“做人做事,信守原则,从不逾越”,“曾三次枪口救人,三次请让考绩给同事”,别人视他为“傻瓜”,他则“始终助人为乐”;“见义勇为,嫉恶如仇,曾冒死检举贪污”;“凡遇操守不良,作风乖僻长官,莫不深恶痛绝,想尽方法回避,即使信托有加,升官升职,亦不接受,甚至立刻求去”,被人称为“不信邪”的标准“湖南骡子”。入台后,他闻知辀重先生逝世,除了将仅存的已经褪色了的辀重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放大,悬挂室内,朝夕瞻仰拈香行礼外,并依大陆家乡习俗于每年中元节另备冥钱化奉,以表崇敬,藉励志节。1979年至1989年期间,他先后发表了《怀念一位伟大爱国的教育家》、《教育之神》和《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等文,对于罗辀重先生之教绩、人格、气魄、志节,述叙甚详,表扬备至。他还在1980年于台湾发起举行了“罗辀重先生逝世三十周年纪念会”,并于1985年3月24日发出《支持大陆恢复陶龛学校的倡议书》,得到了海内外,特别是港、澳、台地区校友的响应。当时国内对罗辀重先生并无深刻认识,但对于恢复一个学校,一个对外极有影响的学校,从统战的角度出发,从上到下都是一致赞同的。因此,从省到市几乎都离不开统战部门参与,有的甚至由统战部门牵头。所以,以李如初先生为代表的台湾校友所作的一切努力和各种建议,很自然地引起了各级领导及广大爱国校友的高度重视,使得复建陶龛学校及兴建罗辀重纪念馆的工作得以克服种种困难,终于胜利建成。可以说:如果没有李如初先生的不懈努力,就没有海外及港、澳、台地区校友的热情支持和积极参与,也就不可能有陶龛学校的恢复和罗辀重纪念馆的兴建。除此之外,李如初先生还身体力行,从经济上率先鼎力相助,并组织校友捐款设立“罗辀重奖学基金会”;并以70多岁的高龄,几度亲自率领台湾校友代表团回母校参加各种庆典,在海内外造成了极大的影响。1996年,李如初老先生不幸患了癌症,且已扩散恶化甚快,在他病危时给我写的自称“告别信”中,还念念不忘母校。他写道:“好在我已年逾八十高龄,一生为人行事,均已勉尽最大心力,可以俯仰无愧。”或许是李老先生一身正气,压住了病魔的缘故吧;或许是他已经做到“俯仰无愧”,心情特别乐观开朗的缘故吧;抑或是他的恩师罗辀重先生在天之灵保佑的缘故吧,总之,经过治疗和休养,李老的病情已神奇地得到控制,健康情况日见好转,至今仍然健在。在此让我们祝愿他老人家健康长寿!李老先生堪称是罗辀重先生最忠实的弟子,铁骨铮铮的血性男儿,他的功绩是不朽的,将永远载人陶龛学校的史册。
陶龛学校的恢复和罗辀重纪念馆的建立,把罗辀重先生从被历史遗忘的角落抬了出来。然而,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对罗辀重先生的认识还只处在感性阶段,纪念馆里陈列的也只是一些不成系统的琐碎零星资料。而对于他毕生从事的教育改革实践和宝贵经验,却很少进行整理总结。但纵使这样,这也是一大进步。
当人们在庆祝胜利的时候,时在娄底地区教科所任职的,被人称“湘中奇士”、“湖南一杰”、“湖南三怪”之一的佘国纲先生出现了,他的敏睿的思维在转动:“陶龛学校为什么办得这么出色?罗辀重先生究竟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指导思想,用一种什么样的方法把它办好的?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能不能加以发扬光大,让所有的教育工作者得到借鉴,受到启发?把所有的学校都办得象往日的陶龛一样好,甚至更好?.....”大凡科学研究工作者都有这样一个习惯,也可以说是一种兴趣,这就是努力去寻求自己所思考的,甚至是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的答案。佘国纲先生开始找到一些介绍罗辀重先生的文章,但大多是—些简短的回忆录之类,仅李如初先生所发表的几篇比较系统,比较详细。但仅是这一些,就让他感到受益非浅,他恍惚发现了一片新大陆,感叹自己 “身在宝山不知宝”,萌发了进一步深入挖掘、研究罗辀重教育思想的想法,他称它是一块“未开发的宝地,是宝贵的人文财富……”,然而,他也知道,罗辀重先生一生没有做过大官,又不图虚名,更何况已被历史湮没了近半个世纪,要研究他,真是谈何容易!—要有时间;二要有资金;三要有精力;四要有能力;五要有勇气;六要有恒心;七要有毅力。然而,越是接近罗辀重,他的时代责任感就越强烈,他说:“也许是我与他(罗辀重先生)心灵相通吧,如果搞实利主义,你不研究,他不研究,我也不研究,那还有谁来研究?如此,罗辀重的生平事迹岂不被埋没?其教育改革经验岂不会失传?如此,我们就会既对不起前人,又有愧于后人。”就这样,佘国纲先生义无反顾地,自觉地承担起了研究罗辀重教育思想的重任。
应该提出的是,对于佘先生来说,他的精力,他的能力,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他的面对困难的勇气是不容置疑的。但时间要自己挤,资金要自己筹集,确实是够苦的了,他却这样安慰我们:“罗辀重先生曾经毁家兴学从事乡村教育改革,为了下一代,直至挤干了自己最后一滴血。与罗辀重先生相比,我这点牺牲算得了什么!”我想,这也是他埋头发掘、潜心研究、四处奔波,默默笔耕的动力所在吧。
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在广大热心人士的支持下,佘先生除了由他主编的《罗辀重教育思想研究》季度小刊早已按期免费赠阅外,还终于编著出了《罗辀重文集》、《教育之神罗辀重》和《基础教育的灯塔——陶龛》三本书,并准备陆续出版发行,今天发行的《罗辀重文集》仅仅是其中的一本。
这里,我要特别告诉大家的是:佘国纲先生既非陶龛校友,又非罗辀重先生的亲属,能如此钟情于罗辀重教育思想的研究,决不是出自偶然的,而是他本身具有一种强烈的爱国、爱民、忧国、忧民的时代责任感,这就是他称之为与罗辀重先生“心灵相通”的精神一血性精神。陶龛校友会会歌写得好:“血性的人都是我们的朋友!”
……
在“罗輈重诞辰110周年纪念暨《罗輈重文集》首发式”上,还有安徽来宾王工先生作了个即兴发言。
王工,原名王兆晃,1929年9月出生于湖南沅江。1939年至1941年,他慕名求学于陶龛学校,深受罗輈重血性素养教育的薰陶。他从陶龛毕业后,上中学、进大学,像罗輈重宁可不当校长也不参加国民党一样,宁可没学上也不参加三青团。1949年,他在中华大学的学业尚未结束就带头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然而不久,他就被动员转业。原因是组织上不相信“国统区”的大学生不是国民党,连“三青团”也不参加?组织说:如果承认参加过,便没事。而他又不愿意违心地承认自己参加过,于是只好背着“历史不清楚”、“可能不老实”的黑锅转业到安徽省蚌埠市。1955年他被证明为“忠诚老实”。然而不到2年,因为“忠诚老实”,他又被划为“右派”,被“无产阶级专政”的手铐铐到白湖劳改农场。1963年,他被甄别平反,成为了“平反右派”,被放到中学当教师。又不过2年,他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做为“大黑帮”给揪出来批斗,直到1978年才被彻底平反,后来成为了国内外知名的“血性律师”,成为了全国七届人大的专职律师代表。他曾在七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书面提议研究、推广罗輈重的教育思想。1990年12月,他收到过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建议的答复”:“您提出的关于‘建议国家教委调查总结、推广爱国教育家罗輈重教育理论、实践’的建议收悉。现答复如下”:“收到您的建议后,我们即责成省有关部门与湘乡市教委、陶龛学校联系,并组织力量进行了初步调查。迄今为止,已找到了近万字的资料”;“经我省有关部门与湘乡市和陶龛学校商议,拟由湘乡市教委牵头,省教科所和陶龛学校参加,对罗輈重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但此后,并不见什么动静。所以,他的发言的题目是:《希望娄底和湖南,象安徽研究陶行知教育思想一样,重视罗輈重教育思想的研究》。
他在发言中“深深企盼湖南省和娄底市不要让安徽专美于前,而致罗重及其素养教育实践和理论的巨大遗产湮没,希望罗輈重教育思想研究首先成为娄底和湖南的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而不是少数人的自发行为,更不是佘先生的个人行为”。
然而,会后至今,罗輈重教育思想研究一直没有成为政府行为和社会行为,仍然是“少数人的自发行为”和我本人的“个人行为”。不过,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罗輈重及其素养教育思想终于被正式载入了官方的教育史册。
那是 2000年10月18日,我有幸被特邀出席《湖南教育史》“省内专家评审会”,另有省社会科学院、湖南大学、湘潭大学、湖南师范大学等10来位教授专家出席。《湖南教育史》于1997年9月正式开始研究和编写,2000年出了打印三卷本初稿。在打印本第二卷,“罗辀重与陶龛学校”被载入“五四前后湖南教育界的璀璨群星”一章中。不过,该章共分四节,第一节为“杨昌济的教育思想”,第二节为“徐特立的教育思想”,第三节为“青年毛泽东的教育观”,第四节为“其他教育名人的教育思想与业绩”。“罗辀重与陶龛学校”仅作为第四节中的一个目,千余字的简单介绍。
我在《湖南教育史》“省内专家评审会”会上,祥细介绍了罗辀重及其素养教育思想,希望《湖南教育史》编委眼光超前,将罗辀重浓墨重彩写进去,得到与会教授专家的一致赞同,领导当即决定将“罗辀重与陶龛学校”由节中的一个目,提升为一节,并指定由我起草。我很快起草了“罗辀重的素养教育思想与实践”一文交稿。这篇一万多字的书稿首先被《湖南第一师范学报》全文刊发,接着被《湖南教育史》采用,将罗辀重与杨昌济、徐特立和青年毛泽东并列为民国时期的湖南教育家。
2002年3月,《湖南教育史》正式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该书三卷本,210万字,装帧精巧,印制精美,被评为全国图书二等奖。罗辀重及其“素养教育”思想被载入该书第二卷,终于被正式载入官方史册。
曾经有位著名的大学教育学教授对我说,要是湖南省教委在落实王工的提案时,把我找去了,那就好了。我想,要是《湖南教育史》初稿专家评审时没有我,那又会怎样呢?世上的事,也许是既有偶然中的必然,也有必然中的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