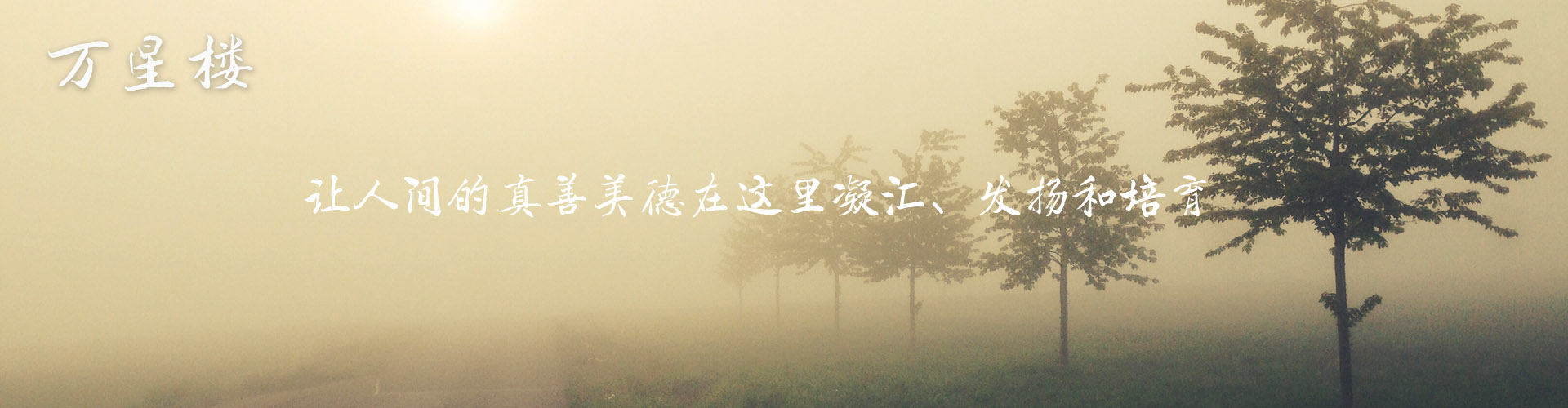罗辀重素养教育叙论
第一章
“素养教育”的应运而生

第三节 一块尚未开发利用的宝地
罗辀重的“素养教育”思想观点与实践事迹自他离世后的近半个世纪中一直被埋没着,而且至今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还是一块尚未开发利用的宝地。它的被埋没,它的不被重视,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他一生一世不做官。
罗辀重从美国留学回国,“当局拟畀教育总长,婉辞”;有人推荐他当国会议员,又谢绝;后来,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又请他到省厅任职,他依然不就。他也当过一次官,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带领学生从军抗日,在73军当了个军法处长的官。1997年,一位94岁的老人柳止一回忆说:“罗辀重当军法处长,我开始认为这与他不做官的一贯思想好象不符。但后来有一次,他与73军军长彭位仁一起由新化到娄底,我们去欢迎,见他一身布衣,横皮带,穿草鞋,精神奕奕。我与他握手,说‘你这么大年纪,从军抗日,真了不起。’ 他摆摆手,说:‘我是无可奈何,如果大家都不动,坐等抗战胜利,那我们就会死无葬地。’ 这时,我理解他了。” 其实,他即便在军队任职,仍然关注着陶龛学校。彭位仁军长十分理解他,特地从新化为他架设军事专用电话线到陶龛学校。
由于无官,也就无权、少机会宣传推广自己的思想和经验。与罗辀重同时代的胡适、蔡元培、黄炎培、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雷沛鸿等,他们要么有点职权,要么活动于国内外大中城市,宣传推广自己的思想主张的机会比罗辀重自然多得多。
罗辀重开始还以校长的身份主持陶龛学校,不久,国民党政府规定:乡校校长必须由国民党员担任。他不愿加入国民党,又不愿放弃改革领导之责,于是让别人担任校长,自己以校董主任之职主持校政,坚持实验。这样,他连个芝麻小学校长的官都没有了,连外出开会的资格都没有了。罗辀重当时没有胡适、蔡元培、黄炎培、梁漱溟、陶行知、晏阳初、雷沛鸿等的影响大,死后更是默默无闻,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二是他的子女和学生中没有大官大款。
罗辀重所处的年代基本上是战争年代。他实施“血性” 教育培养的学生最突出的一点,就是爱国。20世纪三四十年代培养的学生抗日爱国自不必说,20年代培养的学生到抗日战争时,正当年富力强,更是身体力行抗日爱国。抗日名将宋希濂就是20世纪20年代在陶龛学校立下报国志。在九年抗战中率领千万将士驰骋万里疆场,浴血奋战,歼敌40000多人,被国民政府授予最高荣誉勋章,还被美国总统杜鲁门授予棕叶自由勋章。特别是在滇缅大战中与史迪威将军,陈纳德将军(飞虎队,十四航空队)天上,地下配合作战,抗击日寇。1980年,他经中国政府批准定居美国后,为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作了不朽的贡献!在美国和台湾享有极高声誉,俗称:“鹰犬将军”。
陶龛学生究竟有多少牺牲在抗日战场,无法统计,但陶龛学生踊跃参军抗战,当时有目共睹,仅1944年秋,罗辀重亲自带领从军的青年学生就有好几百人。罗辀重除了本人参军外,还把3个女儿送到了部队,大女儿罗光缨还曾乔装乞丐深入敌后。解放战争时期,王工等一大批陶龛毕业生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罗辀重又将自己另外2个儿子罗光盟、罗光益和女儿罗光玺、罗光玖送进了人民解放军。
罗辀重培养的陶龛学生近5000人,在他生前大都与之保持联系,他死后,校友们失去了联络核心,大都互不知音讯,直到1984年前后为重建陶龛学校才重新互相联络上的,也不过500来人,约十分之一,他们大都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了,遍布全国21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英国、印度、巴西、新加坡,以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他们中既没有当大官的,也没有发大财的,大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教授、教师,从事新闻、艺术工作的总编辑、记者、书画家,从事工程建设的高级工程师、经济师,从事行政工作的干部,和各企事业单位的职工,还有不少农民。罗辀重在世的儿女、孙辈,也都是普通职工。他们由于“血性” 的薰陶,“在事业上都是克勤克俭,兢兢业业的;在处群上没有投机钻营、弄虚作假的嗡嗡营营之辈。特别是十年浩劫时,陶龛学校校友,始终保持为人的本色,既未出政治掮客扒手,也未出打、砸、抡的‘左派” 分子”。但他们要把湮没了近半个世纪的罗辀重的“教育的革命” 思想与实践重现于世,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古往今来,中国的学者如不身居高位,又无天时地利可藉,其子孙门徒也无足够能力为之推挽的话,那么其事“湮没不传”,“后生小子,至不能举其名姓”的“可哀”局面是难免的。1950年,曾有一位陶龛教师在罗辀重去世后于学校内设立过 “罗辀重纪念室”,但没有多久便不复存在。1984年前后,以陶龛台湾校友李如初先生等为首,发起重建陶龛学校,颇为热闹了一阵子。但随着经费的缺乏和李如初等老人相继离世,热闹的场面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三是他自己不愿张扬。
“教育的革命”是科学,科学是扎扎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
罗辀重在举世闻名的哥伦比亚大学专门研习过儿童教育,又一手主持过一所小学几十年,却还认为自己“本不是研究教育的,对于教育学术并无素养”,“比较满意的成绩,尚渺不能得,所有精力,实在等于白费” ,只有些“实际经验” (《师范教育放言》)。 1936年,他曾将一些经验公诸于世,在《长沙市教育》和《江苏教育》上发表洋洋上2万言的“师范教育放言”,结果引发了一场大讨论。在这场讨论中,他虽然获益不少,但也使自己以后更加谨慎。1937年,他应《湖南教育》之约,撰写了《一个乡村小学的写真—湘乡陶龛学校概况》,只是具体介绍陶龛学校各方面的状况。此后,很少发现他在各地报刊发表言论,其“教育的革命” 的心得体会文章,也大都发表在自己创办的《陶龛旬报》上。
1943年初,陶龛校友会在校友节上发起捐款编印辀重先生言论集,要他自己写“序”。他觉得这是“一件矛盾的事”,自己“无意且无力,更且不配编印什么集子”,但又不愿在陶龛“受过基础教育的校友,一出校门,便将小时所受训练完全忘却”。为了解决这个矛盾,他与校友会约定:集子仅发给校友,决不出售。
罗辀重将自己的言论集取名《老青集》。他没有写“序”,而是弄了个“前置词”。他在“前置词”中说:“青色可以镇定神经,恢复元气。某种种子,在阳光下普通要8天才能发芽,如果放在青玻璃之下,两天便长出来了”;“青色是冷的,但等到‘炉火纯青’时,又是热度极高的,足见青不是‘温性’;并且青色是不会消褪的,愈久愈青,可能变为老青”;“青年是因他们如草木之方青,但与年龄并无多大关系,年老心不老,还是可以称青年的,所以吴稚晖先生被称为‘白发青年’”;“这些是我喜爱青色,喜爱青年的主要理由”;“我虽然年已半百,日杂儿童群中,不知老之将至。刚好这里征集的,是一些幼稚的作品,多半是对青年以下的人说的,就取了‘老青’二字来名本集”。
世界上的事,无独有偶。古代孔子仅有其对弟子的语录《论语》传世,陶龛校友仿《论语》编印《老青集》。该书1944年由江西青年正气出版社出版,印数很少。遗憾的是,这本《论语》式的《老青集》,我们至今还未找到。当时经办此事的校友现在无法找到,可能都已离开人世,在世的校友大都说只见到过,并不曾拥有过。
四是他过早离开了人世。
罗辀重于1950年清明节自溺于陶龛校内池塘。他本不会这样过早离开人世的。他的 “教育的革命”思想是爱国的.民主的。当时,他虽然不参加共产党,但也不参加国民党。他主持的陶龛学校聘任的教师中就有陈明.李品珍.陈素.刘汉英等共产党员。早在廿世纪三十年代,他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对象。他临死前还被特邀参加湘乡县人民代表大会,出席益阳地区教育行政会议。他的死与他的弟媳直接相关。
罗辀重的四弟早年病故,弟媳周某曾经在长沙与一男人勾搭,犯了族规,被罗家祠堂判三年不准回家。罗辀重见她拖儿带娃在外不便,说服族人,不到三年就将她接了回来,其田产由罗辀重代管,其生活费用由罗辀重负担。1949年底,她老毛病复发,与一南下的土改工作队员勾搭。在这个南下的土改工作队员鼓动下,她向罗辀重要自己的田租。罗辀重告诉她田租都用来办陶龛学校了。她不甘心,当罗辀重从益阳开会回来,正好土改工作队负责人外出开会,便与相好的土改工作队员带头发难,散布流言蜚语,说罗辀重是“大地主”、“伪善人”、“封建卫道士”。他们不仅把矛头指向罗辀重,而且指向其他教师,指向陶龛学校。罗辀重决心以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同事,保护陶龛学校。他溺水而去,是告诉人们他不是“自尽”,而是投身于“教育之水”;他选择清明而去,为的是表明自己的清白。
也许罗辀重稍微坚持一下,土改工作队的领导一回来就会没事了。但罗辀重不可能这样想。当那个南下的土改工作队员对他说,你办学四十年,收了那么多学租、学费,要他立即交出黄金,否则就要开大会斗争他这个“善霸”,他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他知道这是共产党的阶级斗争政策,连晋西北临时参议会副议长刘少白都被武装押送回老家黑裕口进行批斗,并当场被政府宣布撤销其副议长职务,还将其家人扫地出门,他一个特邀出席县的人大代表的人岂能无事。他觉得只有自己选择尊严的死,那种侮辱人格的事才不会落到自己身上;他相信他的死,也许能换取刚刚建立的人民政府善待他的同事、学生和家人。有位工友看到过他写的遗书式的东西,里面说自己“一家十几个人吃饭,却没有一个种田的”,说自己“眷恋涟水河”,要“清明而去”,总觉得是件不祥之事,于是多了个心眼,每天都随时注意辀师的行踪,特别是晚上将面对涟水的大门牢牢地锁上。然而,想不到的事,罗辀重竟在清明夜里自溺于校园内一个几近干涸的池塘。
罗辀重去世后,如他所愿,当地政府一时并没有再追究他的同事和家人,并从优安葬了他,数千人送葬。当时的中共湖南省委副书记高文华听说罗辀重去世,“不胜惊讶与挽惜”。不过,陶龛学校不久即收归国有,改名为“白鹭湾完小”。而陶龛学校校长罗彦谋等还是没有逃过1952年“土改复查”的厄运。
五是世俗观念的影响。
有一种世俗观念:要推出一位鲜为人知的历史人物,如果推荐者不是大官、大名人或者外国人,而是一位普通老百姓,被推荐者不是大官大款,而是山乡俚士,那么即使他再好、再有价值,也很难得到官方的重视和世人的认可。
2010年2月,有人(王旭明)在“腾讯教育博客”发表博文说:“时下,自封为教育家的人不少,被人称做教育家的更多。今天,我听到新华社的消息说,1月11日至2月6日,温家宝主持召开五次座谈会,就正在制定的《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发展纲要》,听取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这点燃起了在心中贮藏很久的想法,以我的标准来看,当代中国堪称真正教育家的甚少,而温家宝是当之无愧的一位。”接着,他提出了“能称上真正教育家”的七大标准:
第一,真正的教育家必须懂政治、懂国情;
第二,真正的教育家必须有属于自己的教育思想;
第三,真正的教育家必须是真心、真诚、深情的热爱教育与学生;
第四,真正的教育家还必须深入到教学一线中去,摸实况,出真招;
第五,真正的教育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保持强烈的批判精神;
第六,真正的教育家不仅仅会挑问题,还要能开良方;
第七,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条,也是许多所谓教育家远远没有做到的一条,就是真正教育家必须努力把自己的思想及时有效准确全面的传达给公众,让公众听明白,想明白,首先要自己说明白。
罗辀重一生一世不做官,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没有人当上什么大官,他没有,也不可能“把自己的思想及时有效准确全面的传达给公众,让公众听明白,想明白”, 这“必不可少的一条”,便将罗辀重关在了“教育家”的门外。
我曾经为罗辀重的研究去找省里一权威教育机构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加以指教。他们说:“佘老师,搞学术研究,就应该像你这样,只是现在象你这样的人太少了。遗憾的是,我们爱莫能助。要是你拿来的是X X X、X X(中央领导),甚至X X X(省级领导)的教育思想研究,那就好办多了。”
我也曾经为罗辀重的研究自费到北京,想当面向教育部的领导汇报,结果不但部长见不到,连一个管科研的司长也不得见,最后把我打发到信访办。信访办的老头很感动,说到他那里去的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而去,而我却是为了一个被埋没的教育家,他答应一定要给我联系到部长,要我等一天。但我等了三天都没有消息,便不再为难那老头了……
我还曾将自己撰写的“罗辀重传略”,投给一“人物”杂志,被一编辑相中,可将近一年未见发表,最后收到编辑的退稿信,说他真想用这篇文稿,但几次讨论都未能通过……
我的《教育之神罗辀重》申请“华夏英才基金”资助,《罗辀重素养教育叙论》申请国家科研经费,结果都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原因大都是评审者中谁也不知有罗辀重其人。《教育之神罗辀重》自费出版后,娄底市社联把它作为全市第一本专著推荐到省社联评奖,据说评委们大都连书都不去看。
2000年10月,我有幸列席《湖南教育史》省内专家评审会,曾提出我认为做为“真正教育家”的4个条件(至少必备其中三个):
一、必须是终身从事教育,“生为教育,死为教育”;
二、必须有自己创造性提出的教育思想理论体系;
三、必须有创造性建立与自己独特教育思想理论体系配套的教育教学制度;
四、必须有其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实验基地,并取得显著的效果。
专家们对我提出的有关“真正教育家”的标准、条件,大多未置可否,只有一位专家在发言中说“罗辀重确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不过,专家们都一致主张将罗辀重与毛泽东及毛泽东的老师徐特立、杨昌济并列载入《湖南教育史》。我想:他们或许这也是一种默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