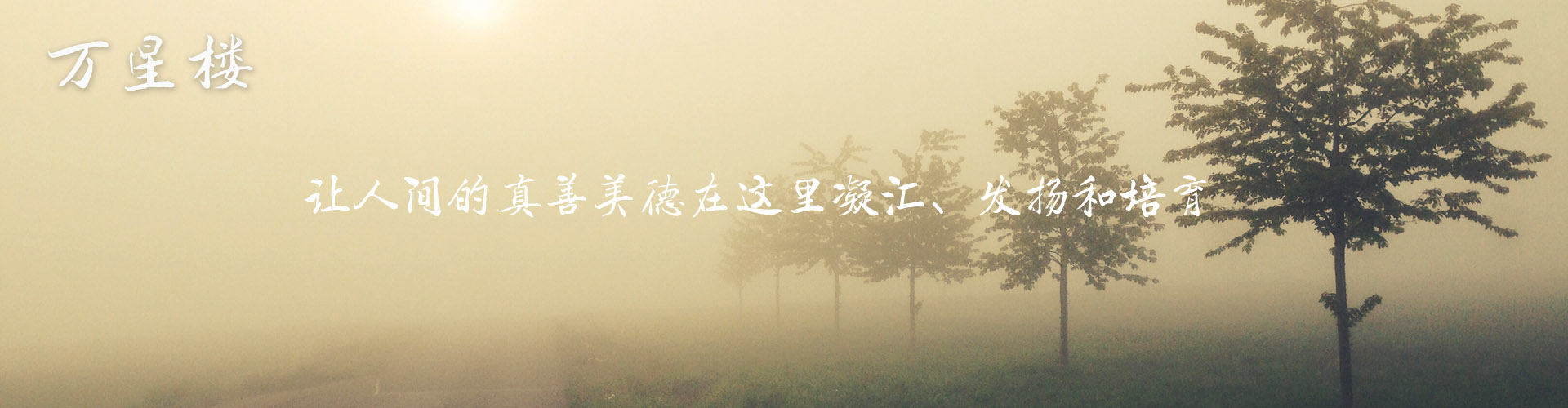当吃饭成为一种负担
来源:端阳史志馆 作者:sheguogang 点击:1124
当吃饭成为一种负担

人的嘴巴有两种功能,一是吃饭,二是说话。肚子饿了就要吃,否则,饿就会转化为饥饿,深度的饥饿可以把人折磨得奄奄一息蹂躏得死去活来。“饿”总是与“吃”紧密相连,在我读过的小说中,印象最深的莫过于阿城在《棋王》里关于吃饭也就是饥饿的描述了。他是这样写的:“(王一生)吃得很快,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常常突然停下来,很小心地将嘴边或下巴上的饭粒儿和汤水油花儿用整个儿食指抹进嘴里。若饭粒儿落在衣服上,就马上一按,拈进嘴里……”
80后90后很可能觉得不可思议,认为那是作者杜撰的情节。他们小时候最痛苦的事莫过于妈妈的强行喂饭了。
年轻人之所以“误读”王一生是因为没有真正体验过饥饿的难受和痛苦,经历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读《棋王》却能读出亲切感和认同感,从王一生的“吃相”上看到自己当年吃饭的狼狈影子。1972年冬天,我跟随社员上山砍树,刚刚费力地砍倒一根杉树,肚子就开始饿了,一连串“咕咕”声从胃的深处直冲喉咙,背上冒出阵阵冷汗。当我背着百来斤重的杉树踉踉跄跄地往山下走去时,饥饿无情地拖住了我的脚步。社员早就下了山,我停下来把树放到地下,将腰上的皮带用力紧了紧,跪到路边大口大口地喝山泉,但驱除饥饿的作用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我要不是鲁莽地吞下了路旁一些不知名的野果,也许会饿昏过去。算我命大,野果并没有毒。那一次,连“喉节一缩一缩的,脸上绷满了筋”都成了一种奢望。
流淌的岁月中,中国人终于将饥饿的历史封存起来,用丰衣足食证明了小康社会的到来。不过,当饥饿的痛苦成为了过去式,“吃饭”的负担又产生了。
我虽然远离官场,但就“吃”而言根本就无法做到“独善其身”,今天朋友请客,明天亲戚嫁女,后天同事生日。“被请”后是“回请”,“回请”后又是“被请”,一旦陷入应酬的循环圈就是没完没了的吃吃吃。对昔日垂涎欲滴的鸡鸭鱼肉不感兴趣了,就变着花样吃新的品种。朋友说从新疆运来的黑山羊味道不错,我们于是驱车几十里光顾“黑山羊”酒店。黑山羊吃腻了,我们又成了海鲜楼的常客。有人介绍蚕蛹的味道不错,我们就吃蚕蛹。当吃野菜成为时髦,我们又成了食草动物。再过若干年,地球上能进嘴巴的动植物估计不多了。
吃来吃去,赴宴不但不是享受有时反而成了沉重的负担。中午同事请客,一堆食物还在肠胃里蠕动,不料一个电话追来了:“晚餐老同学请客,他去年就提处长了,早就说过要请我们的。一定要来啊。”我当然不能退缩,哪怕是刀山火海也要扑上前。下班后匆匆赶到酒家,一阵寒暄后就是开吃了。我望着一大桌美味佳肴实在没有半点食欲,只好象征性地伸伸筷子吃点蔬菜。好不容易应付完晚餐,再次接到邀请电话:“晚上8点到河边吃夜宵,我开车接你。”还不等我回话,电话就挂了。没办法,只好再次“赶场子”。螃蟹龙虾猪脚臭干子等等摆了满满一大桌,我只好偷偷地苦笑。“味道如何?”“还算可以吧。”“什么意思啊。”朋友有点失望。他其实不懂我的烦恼,我这时候吃啥都是索然无味,渴望的只是一碗米汤泡饭而已。
我的口味越来越刁,食量越来越小,啤酒肚却越来越大,体检中发现的毛病也越来越多,朋友圈子里有人还吃成了“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三高”干部。
当吃饭成为一种负担,我有时倒是很怀念当年在乡下过的那种半饥不饱的生活。我们食欲旺盛而生活条件又十分艰苦,一碗比平时多放了些猪油的白菜到嘴里都成了美味佳肴,偶尔弄到一条鱼或者一块肥肉更是成为狂欢的理由。当我们端坐在热气腾腾的饭菜旁的时候,眼睛闪闪发亮,呼吸变得急促起来,风卷残云般的大嚼大咽后,菜汤都不剩下一滴。唉,好久没享受过这种吃的乐趣了。
发布时间:2010/6/26 【打印此页】
上一篇:宁夏归来谈文明
下一篇:千万别低估了小康洁的价值